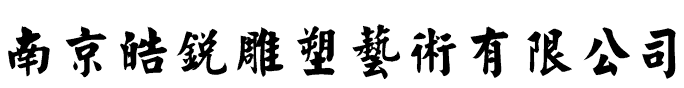《現(xiàn)代雕塑的變遷》與《形而上下——關于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雕塑的哲學與詩性陳述》的比較閱讀(二)
2018-11-12 來自: 南京皓銳雕塑藝術(shù)有限公司
選點十:超現(xiàn)實主義
《變遷》:
1920年,布勒東開始了對“超現(xiàn)實主義”一詞的堅定追求。
他因此堅信,無意識產(chǎn)生所需的動力完全不同于清醒的頭腦。
布勒東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立場堅信不疑。
布勒東的“客觀”概念出自無意識力量。它可以顯得毫無緣由,同時卻又意義非凡。像是來自無意識的啟示。
《形而上下》:
生命:本能記憶與莊子
在理性的邏輯思維方式被顛覆和破壞之后,一直被壓抑著的人的生命潛意識就開始活動起來。弗洛伊德是潛意識學說的開拓者,而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則是真正深刻的東西,是理解人類文化現(xiàn)象的重要的概念!毫無疑問的是,藝術(shù)的根是深植于人類集體無意識的原形或核之中的。
現(xiàn)在我們再來看看莊子與超現(xiàn)實主義。《莊子》中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的故事、夢蝶和魚的快樂的故事,可以說是比弗洛伊德早2000年的潛意識寓言。它們形象生動地表達了通過抑制顯意識,進入潛意識,而達到的創(chuàng)作、生活和精神的極高境界。
點評:關于潛意識與超現(xiàn)實主義,《形而上下》與《變遷》的不同在于,唐堯的背景上多了一個汪洋恣肆的、非理性和潛意識主義的古代中國鼻祖——莊子。
《變遷》:
大多數(shù)超現(xiàn)實主義雕塑本質(zhì)上都稍帶淫穢和虐待狂的嫌疑。這些作品中還有反復出現(xiàn)的暴力主題。
《形而上下》:
超現(xiàn)實主義通過潛意識進入的是人的被壓抑了的本能和欲望的層面,它呈現(xiàn)為精神病和噩夢式的氛圍和場景;而莊禪精神進入的是生命和自然的統(tǒng)一和諧的層面,所呈現(xiàn)的是生香活意的大美之境。這是人欲境界與天地境界之間的差異。
《變遷》:
超現(xiàn)實主義是布勒東對抗實證主義的武器,是他攻擊“資產(chǎn)階 級理性主義”的方式。加博的構(gòu)成主義是理性主義的徹底支持者,所以這兩種運動明顯是思想意識上的敵人。
點評:《變遷》這一段特別鮮明地揭示超現(xiàn)實主義與構(gòu)成主義的本質(zhì)對立。
《形而上下》:
從立體主義的顛覆到構(gòu)成主義的秩序——這是現(xiàn)代雕塑史理性的一翼;而從達達主義的解構(gòu)到超現(xiàn)實主義的沉冥——則構(gòu)成了現(xiàn)代雕塑史非理性的另一只巨翼。他們共同完成了雕塑領域中對于整個世界的理解方式、闡釋方式、交流方式、表達方式和價值判斷的顛覆和革命。現(xiàn)代主義雕塑藝術(shù)的巨大雙翼就這樣生成并展開了。
點評:《形而上下》將構(gòu)成主義和超現(xiàn)實主義視為理性和非理性的兩只巨翼,它們共同構(gòu)成現(xiàn)代雕塑向形而上下、鯤鵬海天的飛翔。
《變遷》:
岡薩雷斯的《頭像》是超現(xiàn)實主義手法與求積法結(jié)構(gòu)的聯(lián)姻,但兩種原型的原始意義都遺失了。求積法賦予了《頭像》一個理性的、可被立即感知的“核心”;而物體的心理與表現(xiàn)主義特性剝?nèi)チ藰?gòu)成主義的機械光暈。
點評:兩種“原型”的表述應該來自榮格。克勞斯認為《頭像》結(jié)合兩者的結(jié)果是兩方面的削弱和消減。唐堯的看法是岡薩雷斯的《頭像》總的屬于超現(xiàn)實主義,對于《頭像》所做的求積法分析實際上是有些牽強的。但岡薩雷斯的金屬焊接作品確實有構(gòu)成主義的傾向。
《變遷》:
20世紀20年代末期,岡薩雷斯嫻熟掌握了金屬直接焊接的制作,可以回避鑄造工序,是更為線性和精 致的造型成為可能。“在新工藝的幫助下,我可以子啊空間中實現(xiàn)作品”岡薩雷斯寫道,“和它一起建構(gòu)。”
“直接—金屬”雕塑的制作技術(shù)包含了將雕塑透明化和開放化的指令。
點評:這一段很有說服力地標書了岡薩雷斯作品屬于構(gòu)成主義的我傾向。也就是說,唐堯同意克勞斯下面說的這句話:或許可以說岡薩雷斯懸置于兩者之間。并不包含任何一方的邏輯結(jié)論。
點評:關于這一句話的表述,有兩個說明:一、是岡薩雷斯而不是他的《頭像》懸置在超現(xiàn)實主義與構(gòu)成主義之間。二、唐堯認為它們反映了胡塞爾哲學對克勞斯的影響,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作為對邏輯理性的反撥,與克勞斯的結(jié)構(gòu)和邏輯方法應該是對立的。
克勞斯的本質(zhì)是結(jié)構(gòu)分析,她擅長這種分析。但在布朗庫西、杜尚、達達、超現(xiàn)實這一翼,由于非理性的緣故,這種分析會被拒絕。克勞斯會感到有一個封閉的、不透明的東西,或者一個空心的表面拒絕她的結(jié)構(gòu)分析。這造成她潛在的挫折感。所以,一旦有機會,比如賈科梅蒂的《懸浮球》,或是岡薩雷斯的《頭像》,克勞斯會立即展開她嫻熟的結(jié)構(gòu)分析功夫。唐堯的《形而上下》則基本忽略了岡薩雷斯的位置。
《變遷》:
賈科梅蒂堅持自己創(chuàng)作的雕塑物體中不存在任何由他參與處理的痕跡。它是欲望的無意識傳遞,而不是精心制作的產(chǎn)物。這些雕塑出現(xiàn)在我的腦海中時,就已經(jīng)是徹底完成的。
帶有色情暗示的《懸浮球》深受超現(xiàn)實主義者們的追捧,因為它把無意識中的能量呈現(xiàn)為具體的特征。“所有見過這個作品的人,都經(jīng)歷了一種強烈而不可名狀的性 欲。
籠子的功能在于將它轉(zhuǎn)變?yōu)橐粋€無法滲透的玻璃泡,懸浮在真實世界的空間中。懸浮球和月牙狀物作為真實空間的一部分,同時又與其隔離,試圖在現(xiàn)實的連續(xù)表面中打開一道裂口。
莫名奇怪,令人不安,這就是“超現(xiàn)實主義物體”。
《形而上下》:
早期的阿爾普和賈科梅蒂似乎就應該被視為超現(xiàn)實主義雕塑的代表。
點評:與《變遷》關于賈科梅蒂 作品精彩的大篇幅分析相對,這次是《形而上下》一筆帶過了應該得到充分表述的賈科梅蒂。正如本文選點二所述“距離”的原因,唐堯在那時并沒有直接感受過賈科梅蒂超現(xiàn)實主義時期的作品。
選點十一:阿爾普和摩爾
《變遷》:
阿爾普寫道:完全自動化的編排,沒有意志力的參與。我把這個過程稱作“根據(jù)偶然的規(guī)律”。“偶然的規(guī)律”包含了所有的規(guī)律,高深莫測,就像是生命起源的造物主,只有在完全無意識的狀態(tài)下才能感受到。我敢斷言,所有遵循這一規(guī)律的人,都在創(chuàng)造純粹的生命。
把藝術(shù)物體看作自然中的一個物種——對自然形式的庫存做出的特別補充。“藝術(shù)是長在人類身體里的一種水果。”
阿爾普從超現(xiàn)實主義轉(zhuǎn)變到基于有機演變概念的立場。
物體光滑表面的輕微凸起和扭轉(zhuǎn),暗示了諸如大理石或青銅之類的我非有機實質(zhì),被一種生命力從物體內(nèi)部控制著。一種表面的不穩(wěn)定性或靈活性,使雕塑體量的外部形態(tài)與剛性核心的相脫離。阿爾普作品中的體量容器由內(nèi)向外表現(xiàn)出流動的壓迫感,使緊張的表面成為反復無常的圖像。20世紀40年代,赫普沃斯和亨利·摩爾在一起形成了有機論雕塑的英國分支。然而,與阿爾普不同的是,他們的作品將有機隱喻推向了構(gòu)成主義美學的理解。莫偶爾和赫普沃斯不再創(chuàng)作絕 對流動的表面,雕刻了更具結(jié)構(gòu)感的體量,外部形態(tài)的每個部分都明顯與一個剛性內(nèi)核相關。另外,兩位雕塑家都非常關注如何賦予自己的作品實際透明性,強調(diào)外部表面與內(nèi)部構(gòu)架的關聯(lián)。這樣,生長的隱喻被理性化,成為對生命物質(zhì)的圖像進行構(gòu)成主義的、結(jié)構(gòu)性的分析。
點評:這里關于摩爾與阿爾普雕塑的結(jié)構(gòu)及理念的差異性分析,非常精到。同是生命的主題再現(xiàn),阿爾普偏超現(xiàn)實(非理性、潛意識),而摩爾偏構(gòu)成(理性、結(jié)構(gòu))。
《變遷》:
與加博和佩夫斯納不同,摩爾從雕刻者的知覺出發(fā),而不是運用脆弱的幾何平面建構(gòu)體量。初看來,摩爾雕塑對構(gòu)成主義機械化的思想意識抱有敵意…但事實上無論何種表現(xiàn)材料,從木材年輪的幾何體到石塊沉積產(chǎn)生的波紋,“靈感”的本質(zhì)都是分析型的靈感。正是類似的透明性影響了波丘尼的《瓶子》和加博的《圓柱》的構(gòu)成,現(xiàn)在這種透明性在此證明自然的實心物體本身也是通過相同的幾何原理形成的。
點評:這里克勞斯繼續(xù)她的結(jié)構(gòu)分析,把摩爾、加博、波丘尼加以比較,并進一步說明摩爾與構(gòu)成主義的同構(gòu)性,值得商榷。
《形而上下》:
摩爾的雕塑語言直承于布朗庫西的形面意識和古瑪雅—阿茲特克石刻的神秘靈性與生命活力。
摩爾的紀念碑,那種深回宛轉(zhuǎn),潛通密貫,包裹山海的渾浩宏闊是整個西方雕塑史乃至藝術(shù)史所罕見的。
我們可以看到一條從羅丹出發(fā),隨著時間的進程,沿著立體主義、未來主義、構(gòu)成主義、達達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向右運動的曲線。這條現(xiàn)代雕塑生成期的運動曲線在經(jīng)歷了二戰(zhàn)之后,以亨利·摩爾為標志,重回“羅丹-布朗庫西”一脈。
事實上,從雕塑語言向泥塑形面回顧并給予生命以存在主義精神審視和終極關懷的意義上看,里希埃和后期的勞倫斯、讓·阿爾普、賈科梅蒂、曼祖都是這一時期歐洲雕塑的杰出代表。我們或許可以暫且將他們統(tǒng)稱為:新生命主義。
而讓·阿爾普自己就是一條從達達到超現(xiàn)實到新生命主義的一條非常清晰的線索。
點評:《形而上下》傾向于把摩爾與構(gòu)成主義摘開,與阿爾普等另列一個從構(gòu)成主義和超現(xiàn)實主義向生命本體回歸的線路。
選點十二:抽象表現(xiàn)主義
《變遷》;
史密斯的作品代表了同代美國藝術(shù)家共有的創(chuàng)作關注。
意在否定當時盛行的觀者與雕塑的交流方式,不是構(gòu)成主義式的智性掌握,就是亨利·摩爾中的感性控制,非此及彼。
點評:克勞斯的意思應該是,史密斯的抽象表現(xiàn)主義既不是純理性也不是純感性的,而是一種綜合體。
《形而上下》:
略晚于抽象表現(xiàn)主義鼎盛的20世紀50年代,美國雕塑家大衛(wèi)·史密斯在60年代登上國際藝術(shù)舞臺。他沒有受過正規(guī)美術(shù)訓練。全部由自己動手焊接的金屬雕塑,從超現(xiàn)實主義的幻想中漸漸呈現(xiàn)出一種介于構(gòu)成主義和抽象表現(xiàn)主義之間的風格。
有一種單純而稚趣的抒情性。
點評:《形而上下》認為史密斯位于超現(xiàn)實主義和構(gòu)成主義交匯并向抽象表現(xiàn)主義發(fā)展的過程中。
《變遷》:
時至1949年和1950年,史密斯鞏固了一種可被稱為極端視覺分裂語法的雕塑語構(gòu)。
作品的兩個主要視圖——正面和側(cè)影——無法用構(gòu)成主義內(nèi)部透明性的模式相互產(chǎn)生聯(lián)系,而在此之前的四十年里,這種模式一直是抽象雕塑的主要構(gòu)造手段。
在《布萊克》中,史密斯拒絕了形式的連續(xù)性,取而代之的是正面與側(cè)面間的分裂感,遵循了徹底不連續(xù)性的原則。
約翰·張伯倫1962年的作品《白絨》,褶皺鋼材的表面膨脹形成巨大的三維殼體。雕塑明顯的中空性確保了觀者不會把表面看做內(nèi)部支架或核心的外在實現(xiàn)。張伯倫作品中四分五裂的鋼板不再具有可供推敲的邏輯依據(jù),使人無法通過視覺分析讓物體變得明了易懂。
正是這種對于分析的明顯鄙棄使張伯倫的雕塑與史密斯的作品發(fā)生關聯(lián)。
點評:克勞斯在史密斯和張伯倫的雕塑作品中看到同構(gòu)的“不連續(xù)性”、“空心性”和無法分析性。
《變遷》:
《白絨》巨大而缺乏細節(jié)的體量使其與20世紀60年代一種逐漸萌生的新感知力結(jié)盟,這不單發(fā)生在美國,還有英國。比如說,菲利普·金的早期作品中也同樣具有這種特質(zhì),單一整體的體量摒棄了內(nèi)部支架,迫使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表面的鋪陳。于是張伯倫和金正在創(chuàng)作的這種雕塑涉入了之后被稱為極簡藝術(shù)的美學領域。賈德作為極簡主義的重要實踐者和代言人,之所以會對張伯倫的作品產(chǎn)生共鳴,是因為他在作品中看到了徹底革新雕塑實踐的可能性。
點評:在這一章中,克勞斯梳理了這種形式變遷的線索:從史密斯金屬焊接雕塑的不連續(xù)性出發(fā),一條經(jīng)過張伯倫作品中空的表面鋪陳的特征,連接到賈德的極簡主義。這個連接好像有些勉強。賈德高冷的極簡主義與張伯倫任性的直接金屬抽象表現(xiàn)主義應該是一種逆反的關系。另一條是從史密斯到卡羅、金和塔克。
《形而上下》:
另一位介于抽象表現(xiàn)主義和波普藝術(shù)之間的美國雕塑家是約翰·張伯倫。他喜歡使用廢棄的汽車殘骸,將它們沖壓折疊再焊接在一起。其中既有一種抽象的張力又有一種意象的頹廢。
他在歐洲的“同志”是新現(xiàn)實主義陣營中的雕塑家塞薩爾。
點評:《形而上下》是把張伯倫放在抽象表現(xiàn)主義和新現(xiàn)實和波普藝術(shù)之間。而在美國抽象表現(xiàn)主義雕塑這條線上還羅列了:考爾德、耐威爾遜、奈基安、蘇維羅等。
《變遷》:
卡羅掌握了史密斯作品中的根本屬性——不連續(xù)性,1960年春回到英國時,開始嘗試焊接。
到了2世紀60年代晚期,卡羅將其作品的材料實質(zhì)強行轉(zhuǎn)為畫意。
一群年輕的雕塑家們追隨了卡羅的腳步,包括威廉·塔克、蒂姆·斯科特。而菲利普·金也從早期對大型靜止的雕塑體量的關注逐漸轉(zhuǎn)向這種繪畫的模式。
《形而上下》:
英國人安東尼·卡羅曾經(jīng)是亨利·摩爾的放大助手,被視為繼史密斯之后鋼鐵構(gòu)成的天才,他氣象恢弘的作品,應該是抽象表現(xiàn)主義雕塑真正的里程碑。
他后來在圣·馬丁藝術(shù)學校任教,學生中有菲利普·金和威廉·塔克,這就使他成為從亨利·摩爾,經(jīng)過金屬的抽象表現(xiàn)主義到英國極簡主義的重要樞紐。
點評:從大衛(wèi)·史密斯金屬雕塑的超現(xiàn)實主義與構(gòu)成主義匯合,經(jīng)過蘇維羅和卡羅們的抽象表現(xiàn)主義,現(xiàn)代雕塑在美國和英國同時走向了極簡主義——形而上絕唱,其背后或內(nèi)置的精神性沖動是極其耐人尋味的。
選點十三:動態(tài)雕塑、波普雕塑、行為藝術(shù)、偶發(fā)藝術(shù)
《變遷》:
時至1967年,對于劇場入侵雕塑領域的不安,被集中體現(xiàn)為一種直接的攻擊。當時邁克爾·費雷德寫道:我想做這樣一個斷言,劇場與劇場性今天不僅正在現(xiàn)代主義繪畫與雕塑作戰(zhàn),而且還在與藝術(shù)本身作戰(zhàn),在與現(xiàn)代主義感性本身作戰(zhàn)……各種藝術(shù)的成功,甚至是其生存,越來越依賴它們戰(zhàn)勝劇場的能力。
對于弗雷德而言,雕塑與劇場的差異關鍵在于時間。這是一種將雕塑的時間性體驗與真實時間合為一體,從而把造型藝術(shù)推入劇場的模式。
劇場性是一個涵蓋性術(shù)語,其中包括動態(tài)和燈光藝術(shù)、環(huán)境和場景雕塑,以及與之關系更為直接的行為藝術(shù)。讓·廷格利1960年在紐約現(xiàn)代美術(shù)館花園里的一場表演。瑪莎·葛蘭姆在活動雕塑的表演中看到了與生俱來的戲劇性。喬治·西格爾或者愛德華·金霍爾茨的作品——是帶有劇場性的。歐登伯格的作品存在劇場性。偶發(fā)藝術(shù)有三個典型特征與阿爾托的戲劇概念有關……
弗雷德曾斷言,劇場性一定會對雕塑產(chǎn)生損害——渾濁了雕塑的獨到之處,剝奪了雕塑性的意義,同時也剝奪了它的嚴肅性。
點評:《變遷》在這一章用劇場性和戲劇性統(tǒng)攝
說明:
1.本文原文來自國內(nèi)著名雕塑家、雕塑批評家、策展人,中國雕塑學會副秘書長、學術(shù)部部長,唐堯的論文“結(jié)構(gòu)變遷與精神歷史——關于現(xiàn)代雕塑的兩種敘事:《現(xiàn)代雕塑的變遷》與《形而上下》的比較閱讀”,有興趣的讀者們可閱讀作者原文。
2.本文僅供學習、參考,不作他用。